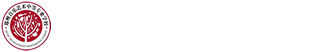舞蹈家--皮娜-鲍什
皮娜-鲍什1940年生于德国的佐林根,少年起开始在福克旺舞蹈学校Folkwang School学习古典芭蕾和现代舞,19岁时到了纽约跟随约斯.林蒙林、保罗-泰勒等现代舞大师学习,以后在1963年回到德国。,经过10年的演员和编舞创作实践,从1973年开始,33岁的皮娜.鲍什开始出任德国的乌帕塔尔舞剧院Tanztheater Wuppertal艺术总监和首席编导,从这时开始,皮娜.鲍什马上着手她的“舞蹈剧场”想法的实现。两年之后,她的根据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春之祭》创作的同名作品立即引起轰动,评论称之为“在约八十个《春之祭》版本中最为突出的”。, 这以后,皮娜-鲍什继续沿着她的“舞蹈剧场”方式创作下去,《穆勒咖啡馆》、《贞洁的传说》、《蓝胡子》、《华尔兹》、《玛祖卡FOGO》、《康乃馨》、《1980》、《窗户清洗工》等都是她的强有力的作品,巡回演出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香港。关于她和她的作品的评信纸很多,大概最为形象和准确的是,“一个未被加冕的舞蹈女皇”。, 皮娜-鲍什至今应该是61岁了,按中国人的说法是"人老珠黄"的那种,从杂志、画册或网上看到她的照片,依然是那种德国美女的美丽的坚硬,面庞线条如被雕刻刀划过,目光始终温柔而炯炯,这种相貌大概也一如她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场景特征:一个美丽少女在一群女孩的簌拥中成为祭品,然后奉献给另一群赤裸强悍的男人(《春之祭》);一个盲女梦游般在堆满桌椅的咖啡馆摸索前行,两个男人在暗处窥视、等街着(《穆勒咖啡馆》);一个全副武装带着滑雪工具的男人在鲜花堆成的小山丘上作滑雪状(《窗户清洗工》)……, 要用文字来描述或解释皮娜-鲍什的作品肯定是徒劳的,它只会使庞博精深的内容流于单一粗浅,让丰富生动的舞台呈现变得枯涩乏味,但我们远离舞台现场,又不得不使用语言传递一些必要的信息让更多的人接近皮娜-鲍什那个充满魅力、让人回味无穷的舞台世界。在为准备这个专辑翻阅手中所有有关皮娜-鲍什的资料的时候,我的目光常常停滞在皮娜.鲍什的单人照片上,她特有的美丽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她特有的神态:安详、平和,即便是烟不离手的形象,你也很难和苦大仇深地进行一个伟大的创作之类联想在一起。我就在想,就是这么一个人是如何把她对人、对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悲伤和荒诞感深藏的作品中的?, 在皮娜-鲍什70年代中期开始让人震惊并关注的作品中,主题方向是,美丽总是柔弱的、她在暴力和强权下永远无助,人世和生活也始终充满被迫和荒诞。皮娜-鲍什的一句简单的表白因此时常被热爱她的人引用:"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一些评论家从皮娜-鲍什么生于残酷惨烈的二战期间、成长于二战后废墟荒芜的德国这种童年和少年经历中寻找她的创作根源,但一个艺术天才必须知识如何把天才的能量释放出来,首先得找到一个通道,皮娜-鲍什找到了"皮娜-鲍什式的舞台方式",这就是后来被评论家定为的"舞蹈剧场"(dance theater)。, "舞蹈剧场"的确是皮娜-鲍什在现代舞上的创举,在舞蹈这么一个始终离不开只靠身体动作来表现的样式(即便是现代舞的开山人邓肯、以及后来的继承者玛沙-格雷尔姆、六、七十年。站在现代舞高峰"的莫斯-肯宁汉等,他们对舞蹈的创造性功绩说到头也只是停留在"自由解放身体"这个层面上),皮娜-鲍什对以往舞蹈方式的改造动作几乎可以说是"破坏"了,她居然让演员在演出中不去做展示身体美和技巧的跳舞,让他们像平常人一样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甚至做出化妆、送咖啡、说话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她的舞台也不像习惯中人们看到的舞蹈演出那么一如既往的干净、清洁、只有诗一般的身体伴随着诗一般的音乐在梦幻的灯光中变幻,令我们陌生的皮娜-鲍什舞台有时候铺满鲜花(《康乃馨》)、有时候搁着桌子椅子、还有浴缸(《玛祖卡FOGO》)、有时候干脆布置成一个生活场景中的咖啡馆(《穆勒咖啡馆》),她的演员不仅跳舞(同样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精妙动作组合),同时也像日常生活中的人那样在舞台上走路、抽烟、打闹、笑、说话、衣着也多半是生活中人常见的汗衫、衬衣、裙子、西装。这种舞台和舞蹈方式注定是要让那些西装革履端坐猩红色大幕前翘首等待高雅梦幻般的身全之舞的人士失望甚至愤怒,所以开初曾经被人视为"垃圾"、"舞蹈的恶魔"。当然现在人们不这么看她了,说起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声音会变得颤抖、眼睛会变得明亮。这就是一个始终坚持艺术创造的力量,一切看似多么强大的抗拒都早晚会被改造的。当然,这种力量首先得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始终不渝。, 对我们这些中国观众来说,皮娜-鲍什居住在遥远的欧洲、德国那边,她近30年的创作基本上发生在欧洲、美国、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应香港艺术节邀请制作的《窗户清洗工》,但这基本上还是与我们无关,她的作品从未在我们能随便去到的地方演出过,她本人也从未来过中国大陆,不过其作品或与此相关的东西曾经多多少少、曲里拐弯地"和我们有关",比如九十年代初在北京,一群人传看她的《春之祭》、《穆勒咖啡馆》录像带,画质非常的糟糕,但一点儿都不影响我们之后的兴奋难眠。1995年在德国路德维希伯格艺术节时,听说文慧要去找皮娜-鲍什的团看看,艺术节的人认真地为她画了一个地图,两天后接到文慧那边打来的电话,声音颤抖的听不清,以为她是在说德语。1997年底在纽约的"下一次浪潮"艺术节上有幸亲眼看到《窗户清洗工》的现场演出,那是在被纽约现如今枯燥单调"玩身体"的现代舞压抑中唯一感觉到的狂喜和解放。之后不久碰到原来广东现代舞团很有舞蹈天份的沈伟,他用秘密的口气通告他已经被皮娜-鲍什的舞团招为演员了(后来知道这完全是单相思)。在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有关皮娜-鲍什的介绍只看到来自欧建平所写,非常珍贵(只是恨他的文字太枯燥)。, 眼下情况似乎有些变化,令人心动的好消息逐渐传来。去年经搞戏剧的易立明介绍,在北京见到了皮娜-鲍什舞团的经理斯美捷特先生,他和舞台设计师一起来北京是为皮娜-鲍什在北京的演出看剧场,计划时间是2004年。太遥远了!前不久和北京哥德学院的魏松先生说起皮娜-鲍什的事,他说也许可以搞一个"皮娜-鲍什作品影像"放映活动,他以前在日本搞过。如果这一计划能实现的话,大概是离我们最近的接近皮娜-鲍什的一次机会。,
皮娜-鲍什1940年生于德国的佐林根,少年起开始在福克旺舞蹈学校Folkwang School学习古典芭蕾和现代舞,19岁时到了纽约跟随约斯.林蒙林、保罗-泰勒等现代舞大师学习,以后在1963年回到德国。
经过10年的演员和编舞创作实践,从1973年开始,33岁的皮娜.鲍什开始出任德国的乌帕塔尔舞剧院Tanztheater Wuppertal艺术总监和首席编导,从这时开始,皮娜.鲍什马上着手她的“舞蹈剧场”想法的实现。两年之后,她的根据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春之祭》创作的同名作品立即引起轰动,评论称之为“在约八十个《春之祭》版本中最为突出的”。
这以后,皮娜-鲍什继续沿着她的“舞蹈剧场”方式创作下去,《穆勒咖啡馆》、《贞洁的传说》、《蓝胡子》、《华尔兹》、《玛祖卡FOGO》、《康乃馨》、《1980》、《窗户清洗工》等都是她的强有力的作品,巡回演出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香港。关于她和她的作品的评信纸很多,大概最为形象和准确的是,“一个未被加冕的舞蹈女皇”。
皮娜-鲍什至今应该是61岁了,按中国人的说法是"人老珠黄"的那种,从杂志、画册或网上看到她的照片,依然是那种德国美女的美丽的坚硬,面庞线条如被雕刻刀划过,目光始终温柔而炯炯,这种相貌大概也一如她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场景特征:一个美丽少女在一群女孩的簌拥中成为祭品,然后奉献给另一群赤裸强悍的男人(《春之祭》);一个盲女梦游般在堆满桌椅的咖啡馆摸索前行,两个男人在暗处窥视、等街着(《穆勒咖啡馆》);一个全副武装带着滑雪工具的男人在鲜花堆成的小山丘上作滑雪状(《窗户清洗工》)……
要用文字来描述或解释皮娜-鲍什的作品肯定是徒劳的,它只会使庞博精深的内容流于单一粗浅,让丰富生动的舞台呈现变得枯涩乏味,但我们远离舞台现场,又不得不使用语言传递一些必要的信息让更多的人接近皮娜-鲍什那个充满魅力、让人回味无穷的舞台世界。在为准备这个专辑翻阅手中所有有关皮娜-鲍什的资料的时候,我的目光常常停滞在皮娜.鲍什的单人照片上,她特有的美丽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她特有的神态:安详、平和,即便是烟不离手的形象,你也很难和苦大仇深地进行一个伟大的创作之类联想在一起。我就在想,就是这么一个人是如何把她对人、对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悲伤和荒诞感深藏的作品中的?
在皮娜-鲍什70年代中期开始让人震惊并关注的作品中,主题方向是,美丽总是柔弱的、她在暴力和强权下永远无助,人世和生活也始终充满被迫和荒诞。皮娜-鲍什的一句简单的表白因此时常被热爱她的人引用:"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一些评论家从皮娜-鲍什么生于残酷惨烈的二战期间、成长于二战后废墟荒芜的德国这种童年和少年经历中寻找她的创作根源,但一个艺术天才必须知识如何把天才的能量释放出来,首先得找到一个通道,皮娜-鲍什找到了"皮娜-鲍什式的舞台方式",这就是后来被评论家定为的"舞蹈剧场"(dance theater)。
"舞蹈剧场"的确是皮娜-鲍什在现代舞上的创举,在舞蹈这么一个始终离不开只靠身体动作来表现的样式(即便是现代舞的开山人邓肯、以及后来的继承者玛沙-格雷尔姆、六、七十年。站在现代舞高峰"的莫斯-肯宁汉等,他们对舞蹈的创造性功绩说到头也只是停留在"自由解放身体"这个层面上),皮娜-鲍什对以往舞蹈方式的改造动作几乎可以说是"破坏"了,她居然让演员在演出中不去做展示身体美和技巧的跳舞,让他们像平常人一样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甚至做出化妆、送咖啡、说话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她的舞台也不像习惯中人们看到的舞蹈演出那么一如既往的干净、清洁、只有诗一般的身体伴随着诗一般的音乐在梦幻的灯光中变幻,令我们陌生的皮娜-鲍什舞台有时候铺满鲜花(《康乃馨》)、有时候搁着桌子椅子、还有浴缸(《玛祖卡FOGO》)、有时候干脆布置成一个生活场景中的咖啡馆(《穆勒咖啡馆》),她的演员不仅跳舞(同样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精妙动作组合),同时也像日常生活中的人那样在舞台上走路、抽烟、打闹、笑、说话、衣着也多半是生活中人常见的汗衫、衬衣、裙子、西装。这种舞台和舞蹈方式注定是要让那些西装革履端坐猩红色大幕前翘首等待高雅梦幻般的身全之舞的人士失望甚至愤怒,所以开初曾经被人视为"垃圾"、"舞蹈的恶魔"。当然现在人们不这么看她了,说起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声音会变得颤抖、眼睛会变得明亮。这就是一个始终坚持艺术创造的力量,一切看似多么强大的抗拒都早晚会被改造的。当然,这种力量首先得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始终不渝。
对我们这些中国观众来说,皮娜-鲍什居住在遥远的欧洲、德国那边,她近30年的创作基本上发生在欧洲、美国、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应香港艺术节邀请制作的《窗户清洗工》,但这基本上还是与我们无关,她的作品从未在我们能随便去到的地方演出过,她本人也从未来过中国大陆,不过其作品或与此相关的东西曾经多多少少、曲里拐弯地"和我们有关",比如九十年代初在北京,一群人传看她的《春之祭》、《穆勒咖啡馆》录像带,画质非常的糟糕,但一点儿都不影响我们之后的兴奋难眠。1995年在德国路德维希伯格艺术节时,听说文慧要去找皮娜-鲍什的团看看,艺术节的人认真地为她画了一个地图,两天后接到文慧那边打来的电话,声音颤抖的听不清,以为她是在说德语。1997年底在纽约的"下一次浪潮"艺术节上有幸亲眼看到《窗户清洗工》的现场演出,那是在被纽约现如今枯燥单调"玩身体"的现代舞压抑中唯一感觉到的狂喜和解放。之后不久碰到原来广东现代舞团很有舞蹈天份的沈伟,他用秘密的口气通告他已经被皮娜-鲍什的舞团招为演员了(后来知道这完全是单相思)。在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有关皮娜-鲍什的介绍只看到来自欧建平所写,非常珍贵(只是恨他的文字太枯燥)。
眼下情况似乎有些变化,令人心动的好消息逐渐传来。去年经搞戏剧的易立明介绍,在北京见到了皮娜-鲍什舞团的经理斯美捷特先生,他和舞台设计师一起来北京是为皮娜-鲍什在北京的演出看剧场,计划时间是2004年。太遥远了!前不久和北京哥德学院的魏松先生说起皮娜-鲍什的事,他说也许可以搞一个"皮娜-鲍什作品影像"放映活动,他以前在日本搞过。如果这一计划能实现的话,大概是离我们最近的接近皮娜-鲍什的一次机会。
温馨提示:内容来源于网络,仅用于学习交流参考,无商业用途,如有不妥请联系本站,将立即删除!
郑州戏曲学校〔郑州音乐艺术中等专业学校,原名河南省王希玲艺术学校〕是河南省专业的豫剧学校,可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像山东、山西、河北、江西、安徽、湖北、新疆等豫剧听众广泛地区学生最多;也是郑州市唯一学历教育戏曲学校,开设有3/5年制升学班,每年均有多名学生被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知名戏曲类高校本科班录取,欢迎报考!咨询电话:155-1616-6613(刘老师)